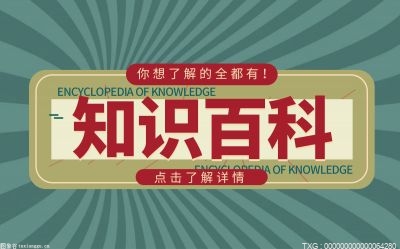銅鎏金木芯馬鐙 以揉拗桑木條做成鐙圈,沿圈條的外壁包釘一層鎏金銅片,上為帶孔的長柄,工藝精細,為唯一有絕對年代可考的完整雙馬鐙。北票馮素弗墓出土,現(xiàn)藏于遼寧省博物館。
本期導讀
在位于朝陽北票的馮素弗墓葬中出土一對銅鎏金木芯馬鐙,這是目前唯一有絕對年代可考的最早最完整的雙馬鐙。作為東晉十六國時期的文物,這對造型簡單的雙馬鐙不僅揭示出在東晉十六國時期,戰(zhàn)場上的騎兵已經(jīng)全副武裝橫沖直撞的歷史面貌,而且還對中世紀歐洲“騎士時代”的誕生產(chǎn)生重要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雙馬鐙從遼西走出,通過草原絲綢之路傳到歐洲。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北燕宰相墓出土的雙馬鐙震驚世界
地處遼西的北票市西官營鎮(zhèn)饅頭溝村原本是一個安靜且普通的小山村。1965年,村子附近一座名叫“將軍山”的山旁偶然發(fā)現(xiàn)的一座晉代大墓,震驚了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
在考古工作者搶救性發(fā)掘中,一座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古墓被清理出來。一段位于中國北方、距今1600余年的北燕歷史也因這座大墓里的珍貴文物而豐滿、生動起來。
古墓中的文物豐富且珍貴。考古人員經(jīng)過綜合判斷,最終得出結(jié)論:大墓的主人是北燕時期宰相、宗室大臣、政治家馮素弗。根據(jù)史料記載,馮素弗死于公元415年,所以,墓中所有文物都有年代可考。
北燕,東晉十六國時期北方政權(quán)之一,定都在今天的朝陽市。雖然北燕政權(quán)存在不到30年的時間,但作為繼前燕、后燕之后的又一個北方政權(quán),北燕對朝陽乃至遼西地區(qū)的歷史產(chǎn)生重要影響。
馮永謙是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當年,他參與了對馮素弗墓的發(fā)掘工作。他告訴記者,因為有人盜掘了古墓,等到考古人員趕到時,主墓室內(nèi)已被盜空,于是,考古人員將沒被盜走的較大文物,如陶罐、石硯、銅虎子等文物取了出來。
在清理墓葬時,考古人員在棺后尾部的泥土里發(fā)現(xiàn)了已經(jīng)散落成碎片的盔甲。按照發(fā)掘計劃,馮永謙做清理工作,在盔甲碎片中,他發(fā)現(xiàn)了一對木質(zhì)包銅馬鐙。
因為在墓中埋藏時間太長,這對馬鐙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腐蝕和殘斷,體形也收縮變小,木芯和外包的鎏金銅片分離,但整體形狀并未改變。馮永謙意識到這是個重要發(fā)現(xiàn),于是馬上畫圖記錄,并小心翼翼地將它們收集在一起,包裝好。隨著研究的深入,最終確定,它為目前世界上唯一有絕對年代可考的最早最完整的雙馬鐙。
馮素弗墓內(nèi)陸續(xù)發(fā)掘出土的文物揭示了北燕時期東西方經(jīng)貿(mào)與文化交流頻繁的重要歷史,也揭示并還原了當時已經(jīng)鮮卑化了的漢人的生活面貌。2006年,馮素弗墓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單馬鐙到雙馬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
如今,馮素弗墓出土的這對銅鎏金木芯馬鐙,正靜靜地陳列在遼寧省博物館內(nèi),供四面八方的觀眾前來觀瞻。
一對其貌不揚的馬鐙,何以成為重要文物?何以引起國內(nèi)國際的廣泛關(guān)注?
在馮素弗墓出土雙馬鐙實物之前,世界各地均未出土過成對的馬鐙實物。從沒有馬鐙,到單個馬鐙,再到雙馬鐙,這個看似簡單的馬具歷史沿革,卻跨越了上千年。
馬,作為一種家畜,由野馬馴化而來。但野馬何時被馴化成為家馬,學術(shù)界仍存爭議。雖然在時間上有爭議,但學術(shù)界在馬的馴養(yǎng)地點上取得了共識,即在中亞,由游牧民族完成。
野馬馴化成家馬之后,馬成為人們生產(chǎn)、生活甚至戰(zhàn)場上的重要工具。但在戰(zhàn)斗中,馬只是戰(zhàn)車中的一部分,換句話說,馬、車、人這三者共同組合而成的戰(zhàn)車是當時的重要武器。
上世紀50年代,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赤峰市寧城縣發(fā)掘出土了一塊周朝時期的刻紋骨板,透過這件文物,可以窺探當時戰(zhàn)車的樣貌。骨板上刻有兩輛馬車,每一輛馬車各有兩個輪子、兩匹馬。這塊刻紋骨板雖然線條簡單,從中卻可以看出戰(zhàn)車中馬匹的重要性。
馬被用作騎行工具始于北方地區(qū)。專注馬具研究的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長田立坤表示,考古人員在遼西及內(nèi)蒙古東部發(fā)現(xiàn)了多處秦代以前車馬器的遺址,比如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赤峰市寧城縣南山根,我省的朝陽縣魏營子、建平縣大拉罕溝、凌源市三官甸子等地,均有發(fā)現(xiàn)。
文獻資料與遼西地區(qū)出土的車馬器、馬具等文物,印證了這樣一個史實——春秋晚期,以游牧為主的東胡族進入西拉木倫河流域,他們成為遼西地區(qū)最早的騎馬民族。而大小凌河流域最早的騎馬民族則是東漢初年的東胡族后裔——烏桓。
雖然東胡、烏桓等游牧民族經(jīng)常策馬奔騰于廣袤的草原與林間,但這并不代表馬鐙也一同出現(xiàn)。
我國最早的“馬鐙”模型出土于湖南長沙,是一組戰(zhàn)馬青釉俑,為西晉永寧二年(302年)文物。在馬的前鞍橋左側(cè),下垂著一個三角形的馬鐙,右側(cè)沒有。這意味著,左側(cè)的單馬鐙只供騎士迅速上馬時使用,騎上馬后,這個馬鐙就不再發(fā)揮作用了,從這一點來說,它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馬鐙。
對歐洲“騎士時代”的誕生產(chǎn)生重要影響
自50多年前在北票馮素弗墓中發(fā)現(xiàn)雙馬鐙后,考古人員在東北、中原地區(qū)的一些墓葬中,相繼發(fā)現(xiàn)了東晉十六國時期銅片或皮革包裹木芯的馬鐙,這其中既有單馬鐙,也有雙馬鐙。在國內(nèi)一些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古代墓葬中,還曾發(fā)現(xiàn)隨葬的陶俑上刻畫有馬鐙的形象。這說明,在東晉十六國時期,全國各地已經(jīng)普遍使用雙馬鐙了。
雖然馮素弗墓出土的這對馬鐙結(jié)構(gòu)簡單、造型普通,但是,它和墓葬中出土的盔甲、馬具等實物一起,共同反映了東晉十六國時期戰(zhàn)場上“甲騎具裝”的盛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對馬鐙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物價值與研究價值。
所謂的“甲騎具裝”,簡單來講,指的是全副武裝的騎馬部隊。在中國古代戰(zhàn)爭中,齊全的裝備可以最大限度保護戰(zhàn)馬與騎兵的安全,不會被對手輕易傷害,所以“甲騎具裝”是當時的重裝騎兵,殺傷力相當大,軍事斗爭進入騎兵時代。
“甲騎具裝”中,雙馬鐙作用不可小覷。因為有了雙馬鐙,騎兵不僅可以騰出雙手揮動武器,還可以借助雙馬鐙控制戰(zhàn)馬,大大增強作戰(zhàn)能力與前進速度,為在戰(zhàn)斗中獲取勝利提供保障。
當然,雙馬鐙的意義遠不止于此。距今1600多年的這對馬鐙所揭示的“雙馬鐙時代”,還對中世紀歐洲“騎士時代”的誕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一位美國學者說:“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馬鐙,使騎手能安然地坐在馬上,中世紀的騎士就不可能身披閃閃盔甲,救出那些處于絕境中的少女,歐洲就不會有騎士時代。”
由此可以看出,馮素弗墓葬中的這對馬鐙,既是我們窺探一個歷史時代的窗口,也是促成西方一個階層出現(xiàn)的重要推動力,可謂影響深遠。
(本版圖片由遼寧省博物館提供)
手記
草原絲綢之路 是連接歐亞的重要通道
朱忠鶴
北票馮素弗墓葬中出土的銅鎏金木芯馬鐙,既揭示出距今1600余年前中國有一個“雙馬鐙時代”,也印證了歐洲“騎士時代”的出現(xiàn)與其息息相關(guān)。
那么,中國的雙馬鐙是通過何種路線傳遞到歐洲的呢?這就涉及另外一個話題:草原絲綢之路。
在馮素弗墓葬中,與雙馬鐙同時出土的還有鴨形玻璃器、碗、杯等幾件精美的玻璃器皿。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經(jīng)分析認為,這些玻璃制品并非產(chǎn)自中國,而是來自遙遠的羅馬帝國。在東西方不斷交流中,鴨形玻璃器等造型別致的器皿從西方傳入了東方,而雙馬鐙等器物則從東方傳到了歐洲。
學者們認為,草原絲綢之路的開通要早于東晉十六國時期。作為連接歐洲與亞洲古老文明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草原絲綢之路橫貫東西,一頭連接歐洲,一頭連接日本列島。具體來說,如果以我省的遼西地區(qū)為中間點,向西經(jīng)過亞洲中部的蒙古高原,穿過中西亞北部地區(qū)后,抵達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地區(qū);向東則直抵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大約在公元前5世紀,草原絲綢之路發(fā)展為十分重要的貿(mào)易通道。
馮素弗墓葬中出土的這對馬鐙的傳播路徑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草原絲綢之路的走向。除了雙馬鐙促使歐洲產(chǎn)生“騎士時代”與“騎士階層”外,雙馬鐙向東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在朝鮮半島,考古人員也曾發(fā)掘出土雙馬鐙實物。不僅如此,這里還曾發(fā)掘出土了羅馬帝國時期的玻璃制品,這也更加驗證了這條草原絲綢之路的存在。
草原絲綢之路不只是貿(mào)易通道,同時還是一條佛教傳播通道。從歷史遺存來看,不論是朝陽北塔、南塔,還是位于義縣的萬佛堂石窟、阜新的海棠山石窟等,如果以時間軸線進行串聯(lián),可以勾勒出佛教傳播通道的走向。
既是貿(mào)易通道,又是文化通道,這條草原絲綢之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進一步深入挖掘其厚重的歷史與文化內(nèi)涵。
制圖 隋文鋒
遼寧日報記者 朱忠鶴
關(guān)鍵詞: 世界上最早
責任編輯:Rex_10